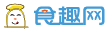2019年5月3日,多云。
(一)
晚上7点46分,一架波音787飞机安全着陆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飞机停稳后,与以往不同,大家都安静地坐在自己位置上。机舱门打开,一个穿着黄色制服的男子走上了飞机,他在我旁边的座位前蹲了下来,问:”女士,你感觉怎么样?”
他询问的对象是我身边的一位空姐,也是我的病人。她把氧气罩挪开,艰难地说:“我感觉喘不上气来”。说完,她把头继续埋进氧气罩里。
我接过话头:“我是医生。她从今早起就呼吸困难,在飞机上走动后有所加剧,吸氧稍微有些帮助。没有发烧咳嗽,体征稳定。”我把手上的一张纸递给他,“详细记录在这里,你可以把它给急症室医生。”
男子接过纸张,说“谢谢你,医生。你觉得她能自己走下飞机吗?”
我:“绝对不行。她需要担架或轮椅。”
“好的。”
两分钟后,又有两个穿着黄色制服的急救人员推着轮椅上了飞机,他们把我身边的病人扶上轮椅。空姐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虚弱地说了声“非常感谢”。我把身上带着的氧气罐卸了下来,最后嘱咐了一句“她需要立即吸氧”。【飞机上的氧气罐必须背在身上。我因为坐在病人旁边,就一直替她背着。而且氧气罐不能带下飞机。所以病人需要到机舱外后重新接上氧气】。
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我松了口气。又不禁担心她去医院后会查出是什么诊断,她会怎么样。我有我的怀疑,但飞机上没有条件让我确诊。
短暂的思绪被周围人起身拿行李的嘈杂声打断,我拿起背包和行李箱,跟着人流下了飞机。
(二)
今天的飞机误点了一个小时,我有些郁闷,因为这意味着我到家时孩子们都已经睡下了。飞机是新型的波音787大飞机,倒很舒适。
坐上飞机后,我泵完奶,看了一遍电影目录,在《徒手攀岩》和《波西米亚狂想曲》这两部片子间纠结了一阵,最终决定选择看《徒手攀岩》。影片开头,AlexHonnold攀上了ElCapitan顶峰,俯瞰大地,深邃的眼睛里闪烁着光,天上几只乌鸦飞过。我心想,导演还挺暖心的,先把完美结局放上来,不用我们接下来提心吊胆100分钟猜测Honnold的命运。
突然,影片的画面被切断,广播响起:“飞机上有医生吗,请按铃告知。”
(三)
一般碰到这种广播,我会稍微等等,因为通常会有别的医生在。而且一天下来我感觉很疲惫,摊在座位上懒得起来。过了两分钟,广播又起,“飞机上有医生吗,请按铃和机组人员联系。我们有一个紧急情况”。广播里的声音略有焦急。这种声音并不陌生,触动了我的职业神经,这次我想也没想立即按下了呼叫铃。
不过10秒钟,一名空姐就出现在我座位前,她说:“请跟我来,是我们的一个机组人员”。我随她到了飞机后方,看到几个机组人员围着一个中年空姐,她正弓着背坐在椅子上,拿着氧气罩急促地呼吸着。
我蹲下,直到能和她面对面眼神交流:问,“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喘不上气”。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天早上,但是上飞机后开始严重起来。我用了几次药物气雾剂(inhalers)但没有什么用”。
她摊开手,给我看她手中的药,是异丙托溴胺气雾剂(Atrovent)和肾上腺素气雾剂。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了解到,她去年底得过一次肺炎,后来一直断断续续有呼吸困难,近几个月基本每月都有反复,吃了一些抗生素,也一直在用气雾剂,没有明显作用。异丙托溴胺气雾剂是昨天新配的,一直在用,没有效果。
她表情难受,呼吸略微急促,但还能说出整个句子,除了呼吸困难外没有别的症状,我心里稍微放心些。
旁边的空姐在电话里跟机长通话,然后扭过头问我“需要让飞机紧急降落吗?”(doweneedtodiverttheairplane?)。
我脑子里闪过她可能的疾病:肺炎,心衰,急性非栓塞,气胸,慢性肺病。
她平时身体健康,没有哮喘等慢性肺病,一直在走动,症状也发生的比较缓慢,所以后面三种可能性很小。从她必须坐起来呼吸才顺畅些,昨晚无法平躺,没有发烧只有干咳这些症状来看,我怀疑心衰引起肺水肿可能性比较大。
空姐接着说,“我们距离目的地还有80分钟,机长问需要转道降落吗?”
我不确定,“现在的情况很难说,让我再看看。”
我看到旁边急症箱里有一个听诊器,是那种很廉价的听诊器。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种听诊器根本听不出肺音。这时,我无比怀念自己用了十年还很好用的Littmann听诊器,可惜没有随身带着。我试着用廉价听诊器听了几下,但劣质的仪器,加上飞机引擎的噪音,根本无法听出任何声音。
我用另一个仪器测量了血压和心跳,血压略偏高:134/102,心跳偏快:103。我拿表测了下她的呼吸速度:每分钟22次,也偏快。
“体温计呢?”这个急救箱没有。空姐去找另一个急救箱。我摸了摸她的额头,感觉不烫。
另一个空姐说,你来前我们让她吃了两粒阿斯匹林,要不要再吃?我说,“好的,吃阿司匹林没问题。但这个应该不是心梗塞或肺栓塞的问题,不用继续吃”。
我看着病人的眼睛说:“我无法用听诊器听清楚你的肺部声音,也无法测量你的氧饱和度。所以我会很大程度上依靠你的描述。你自己感觉如何?”
她说:我只要吸着氧气不动就可以,我可以撑到飞机降落。”
我说:“你不要硬撑,不要考虑别人,现在你的健康最重要。如果你感觉很不舒服,我们应该尽快把你送到医院。”
她说,“我没事,休息一下就可以了。我不想降落在别的地方,我的家人都在洛杉矶。”
我看她神志清楚,呼吸也渐渐平静下来,就叫空姐对机长说先不用紧急降落。
旁边的空姐说,“我把你们送到商务舱坐下吧,舒服一些。医生,你能坐在她旁边吗?”
(四)
我陪她在商务舱坐下,短短的一段路程走下来,病人的呼吸困难又加重了。空姐们看她的样子,再次担忧地问我,“你认为飞机需要降落吗?”
我心里也十分纠结,一方面我知道,不论是什么原因,她的呼吸困难都会因为走动而加重,所以这不奇怪。但另一方面,我确实无法知道她能撑多久。如果我能听到她肺部的呼吸音,心里会更有些底,但不给力的听诊器,或者说我被高级听诊器惯坏了的不给力的耳朵,无法帮我做出判断。
我盯着她脸部的神情和颈部随着呼吸的起伏的肌肉,希望能从中看出一丝线索,判断出她能不能再撑一个小时。
我说,再观察五分钟。
病人也有些紧张了,问:“我怎么又感觉无法呼吸了,我是不是有惊恐症(Panicattacks)?”我摸着她的背,安抚她说,“虽然我无法确定你得了什么病,但很多病症都会在运动时使呼吸困难加重,深呼吸,多吸几口氧气,会好起来的”。
幸运的是,五分钟后她的情况有所好转,我决定,飞机不必紧急降落。
接下来的近一个小时,时间过得很慢。终于找来了一次性温度计,测量了一下,没有发烧。病人在吸氧的间隙,问了我一些问题:
“我有可能是什么病?”
“可能是肺部也可能是心脏或是别的原因,进一步确诊需要进一步检查。”
“医院里会做什么检查?”
“血检,肺部X光片,又可能需要肺部CT,和心脏彩超。”
“我为什么嘴巴这么干?”
“氧气面罩吸氧会让你嘴巴发干,不要担心。”
“我不会有事吧?”
“你不会有事的。”
(五)
在飞机上,没有了随处可见的电脑,没有了昂贵的仪器,我的问诊比很多时候在医院还详细。
我想起几年前自己在非洲的经历:那里的医院只有一台X光片机,很多时候还没有胶片。血检也是昂贵的项目,所以除非必须的情况尽量不做。那里的医生曾骄傲地对我说,他看病人的眼底(结膜)颜色,就能知道病人的血红蛋白有几克。后来,我也学会了这个技能。
现在坐下来写这篇文章时,我又想到一些当时可以用的体检的方法,比如听肺部的EtoAchange,percussion等方法,但由于长时间没用,当时一下没想到。随着仪器的先进,医生查体(physicalexam)能力的退化是必然,也有些可惜。
回到飞机上,没有了检查仪器和药物,甚至无法确诊的情况下,关怀和鼓励成了我唯一的药方。
“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着陆了”。
“你做得很棒,你非常坚强”。
“嘴巴干是正常的,喝口水吧”。
“到了地面,救护车会把你马上送到医院。”
拍拍背,递个水。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我盯着面前的屏幕,7点46分,飞机终于着陆。我悬着的心也落地了。
本文转载自其他网站,不代表健康界观点和立场。如有内容和图片的著作权异议,请及时联系我们(邮箱:guikequan@hmkx.cn)
原创文章,作者:芒小种,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fhgg.net/shenghuobaike/57882.html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食趣网】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fhg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