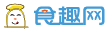属于我们的青葱岁月
一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我被部队派去北海舰队第一训练团参加为期六个月的信号专业学习。与我一起去的还有另外五名新兵战友,都是十八九岁。其中三个是荣成人,两个是沂水人。
我们去训练团三大队十八中队报到,中队长应声走出来,看过介绍信后,他满面春风地对我们说:“欢迎你们来学习!我叫李春生,是十八中队的中队长,你们以后叫我李队长好了。”听了李队长开门见山地自我介绍,我们六个人你看我我看你,然后由我开始依次地向李队长报告了我们的姓名。李队长喜笑颜开地把我们领到了三小队的门前,大声喊道:“施大安!”“到!”一个年轻帅气的矮个军官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李中队长说:“这六名陆军新战士是来学信号的,我把他们交给你了,你可要照顾好他们啊!”“请中队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看着小队长向中队长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中队长这才笑着原路返回了。
施小队长叫来一名老兵班长,他说:“你去安排一下他们六个人的吃喝拉撒睡吧!”老兵班长也姓李,话不多,立正回答了一个“是!”之后,便转身去张罗着安排我们六个人的床铺,并且把我们介绍给了同宿舍里的海军战友。一旁观望的海军战士好奇心极强,他们都想知道陆军为啥来海军这?并且还住到了一起?为啥也来学信号专业?
正当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小队长走过来了,他看出了战士们的心思,愉快地回答了大家的疑问,他说:“陆军也有船艇部队,也需要信号通信。”他见战士们似懂非懂的样子,又补充一句说:“你们和他们除了身上穿的军装不一样以外,其他的都一样,你们都是来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不对,现在你们都统统叫‘学兵’。”说完,小队长来到我们几个陆军战士面前,用明亮的眼神认真地扫描着我们每六个人。接着,他笑着说:“你们陆军战士听好了!我现在宣布--徐承彬为你们陆军班班长,赵连海为副班长!”赵连海是谁呀?他就是两个沂水人当中的一个。施小队长说完了话,就开始招呼一旁围观的海军战士来帮我们整理内务。
在这些热情奔放青春洋溢的海军战士们中间,有一个叫徐玉洲的人显得格外殷勤十足,他是海军新兵班班长,掖县人,可能因为他跟我都姓徐的缘故,我俩一见如故,彼此心生好感。后来在我们结业前,他要改名换姓,找我帮他起过名,这是后话。
我们来的当天,午饭在车上吃过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跟着海军战士们一起站着队、唱着歌,一起去餐厅就餐。说是餐厅,实际上就是一个大一点的空房子,里面用砖砌成的墩子上挡起一条水泥板,一条又一条地就成了简易的餐桌。战士们端着碗排着队去打饭,然后再站回自己的位置上就餐。
虽然说战士伙食费不高,但是馒头米饭管吃。每人两勺子菜,无非就是白菜、萝卜等时令蔬菜,连汤带水的,好在每个人碗里都能分得一两块猪肉。听说,这猪肉是训练团养的猪杀的,专门用来改善战士们的伙食,所以吃起来格外觉得香,好吃!我们吃完了饭,要自己刷碗筷。开始吃一两顿饭,还没觉到有什么不对劲,等吃上几天后,再去刷碗筷时,就觉得碗筷黏糊糊的怎么刷都刷不干净了,原因是炊事班炒菜、熬汤用的都是猪油,再加上没有热水洗碗,所以每个人的碗筷都油乎乎的,好在每人都有两只碗,刷完了把两只碗上下一扣就看不见碗里面的油垢了。
二
十八中队有三个小队,都是学观通的,分为“报务、雷达、信号”三个专业,所有专业都是根据部队作战战位需要安排的。虽然各小队长管理自己小队的日常事务,但是每天早操后还是要集合在一起听中队长训话。别看着中队长平时笑嘻嘻没脾气,可是到了他训话的时候,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特别严肃。他每天都是照例对军容风纪进行重点讲评,对各小队上报的好人好事进行口头表扬。他说一口天津话,听起来特别好听。他总是在训话之后说一两个笑话给战士们听,让大家在哈哈大笑中受到教育。
有一次,他说:“有一天早上,我蹲茅坑刚准备解手,有个学兵进来就问我‘中队长,您吃了吗?’问的我说吃了也不是,不说吃了也不是!所以,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今后我们说话要讲场合,不能随便乱说乱道!说话是一门艺术,也是人与人交流的一种方式,我们既要讲好文明用语,也要注意用词得当,不然非闹笑话不可!”
从那时候开始,我知道了说普通话和讲文明用语的重要性。我们这些刚踏入部队的新战士,就是从学说文明话开始了军旅生活。
我们学的信号专业,因为要眼睛看和脑子记,所以必须从汉语拼音学起,也就是“通文”。我们每天站着队喊着口号来到教室学习。教我们通文课的是位中等个头五十多岁的教员,他姓于,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温文尔雅。我从他的谈吐中得知他知识渊博,我总感觉他教我们汉语拼音是有点大材小用了!可是于教员从来不摆知识分子的架子,他给我们上每一堂课都很认真,并且他还经常跟战士们互动,课堂上时不时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和热情的欢呼声。有一次,教员给我们出了一个上联“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让我们对下联,可是,我们对了半天也没有对上,真是太有意思了!如果是现在的话,我还真能给他对上几个,比喻说“山东落花生花落东山”“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等等。
通文课的目的就是把汉字用拼音拼出来,再用长短不一的光和部位来表达出来,比方说“a”这个拼音字母,要念“啊呀!”用“滴”和“嗒”一短一长来表示出来,对方就能知道信号是“a”的意思,其他拼音字母也都有固定的念法和表示方法,因为这些都属于机密,在此不宜多述。于教员要求我们都用信号方式阅读报纸,说是如果能用信号方式把一张报纸流畅地读出来,就算是合格了。于是,战士们就刻苦练习,不论是上课还是下课,到处都能听到战士们在喊“嘀嗒--嗒嘀嘀嘀--嗒嘀嘀嘀--嗒滴滴……”的声音。
我们第三小队的海军战士都来自掖县(现莱州市),口音跟我们文荣大不一样,所以我们私下里就叫他们是“老西子”,这些被我们叫做“老西子”的战士普遍学拼音的成绩都不如我们。于教员上课时经常表扬我们几个发音准确,尤其是重点表扬我,说我的通文考试成绩每次都是第一名,如果大家都能像我一样,那就太好了。海军战士们见教员经常表扬我,都有点羡慕嫉妒,私下格外地用功学习,都想被教员当众表扬一顿,可是越是这样,教员越是不轻易表扬他们。因为他们努力的同时,我也在加油学习,所以我的通文成绩一直还是第一。到了通文课结业的时候,于教员又当着全体学员的面,重点把我表扬了一番。
三
学完了通文课,我们都想放松一下自己。有一天,我在操场上散步,被盛开的月季花吸引住了,正看得入神时,被中队文书叫住了,他说:“王指导员找你有事儿。”我慌里慌张地去了,王指导员见我紧张得满脸通红,赶忙给我倒了一杯水喝。他说:“我没啥要紧事儿,就是听说你老家文登有种西瓜的,是吧?”我一听脑子里飞速地搜索起西瓜来,然后回答他:“有,不是很多。”“没事儿,我老家有个亲戚他想种西瓜,你看能不能让你家里人给弄点西瓜种儿,我花钱,让他试试?”我满口答应下来,回去赶紧写信给公社驻地村的朋友问询,并让他一定想办法把这事儿办成了。
时间过了半个多月,朋友寄来了一个包裹。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些带壳的花生,还有一小包西瓜种和一封信。信上写着西瓜种子名叫“蜜宝”,二两多,不要钱。我高兴极了,赶紧把花生和西瓜种子给指导员送去。指导员接过西瓜种子,说:“太谢谢啦!西瓜种儿我留下,花生你留着自己吃!”我像完成了一项光荣使命似的高高兴兴地把花生拿回宿舍,跟战友们一块吃了。至于西瓜种子“蜜宝”在指导员亲戚家的地里长成啥样子?我一直想问,但没有敢问。
很快,我们开始学灯光课了。灯光是由短短长长长长短短变化多端的灯光组成的,需要把通文课上学到的知识灵活地运用到灯光课里来,这需要脑子灵活反应快,不仅眼睛好还得把看到的长短不一的灯光翻译成汉字和文句来,不下苦功,很难学会。
我们的灯光课分室内课和室外课两位教员担任。室内课是一个矮个头不苟言笑四十来岁的男教员,他说:“我姓史,历史的史。”简洁明了不啰嗦。史教员上课有个特点,就是不点名也不提问题。他总是坐在讲台上,用发报的姿势按着发报器,挂在黑板上的是一个广播匣子大小的东西就一闪一闪地亮起来,他要求我们:“我在上面发,你们在下面喊出拼音是啥就行。”于是,教室里的喊声此起彼伏。越这样,他发报的劲头就越足。我们就是在这种学习氛围中了解了灯光信号的秘密是由长短不一的光来表现的。史教员从来不问我们懂不懂,知不知道?他只是一个劲地发,让我们一个劲地喊,从我们的喊声中他就能听出来我们喊得对还是错。等到我们都喊累了,他也发累了,下课的时间也就到了。
我们都很喜欢他的教学方式,靠我们每个人的自律,不靠教员管教。就这样,室内灯光课在我们的叫喊声中圆满地结束了。
夏天到了,合欢花盛开的时候,我们也从凉爽的教室里来到了阳光灿烂的大操场上,开始了室外灯光课程。室外灯光课就是一直在大操场上站立的那种,无论是大风天还是大热天,都得老老实实站着不许动。担任我们的室外灯光教员是一位长得很帅很高很年轻的教员,他叫冯强,战士们都很喜欢他。我为啥记得这么清楚,原因是我们后来有过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也是后话。
我是陆军班班长,经常担任小队值日长,我每次把队伍带到操场后,都要先向冯教员行礼报告。尽管他告诉我不戴军帽的时候,可以不行军礼,但是我老是忘,于是他就老是笑,就这样我们加深了彼此的印象。每次等我报告完毕之后,他看着队形散开了战士们都站到了各自的位置,他才再健步登上高高的信号台,开始他的灯光实操课。他先从我们的汉语拼音开始,每天都要考一遍试。在考试之前,他会事先告诉我们变换成二人一组的队形,一人收看信号,另一人记录。考完上组,接着考下组。上次记录的人收看,上次收看的人负责记录。就这样,我们风雨无阻地在操场上练习了一个多月的收看拼音字母,然后才开始练习收看简单词句,再后来才是一句长话,最终规定合格标准为一分钟收看十五个汉字,必须准确无误。
就这样,在太阳底下练兵习武,我们渐渐晒成了黑人,暴露在外面的皮肤也都晒爆皮了。冯教员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说:“你们平时多流点汗,战时就少点流血!皮肤晒黑了不要怕,这说明了我们都很健康!”我们看到冯教员的脸也晒得跟流油似的,战士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训练辛苦了。跟我一组的是一位荣成战友,我俩在收看拼音的时候经常出错,总以为自己看得对,对方记得不对。好在最后灯光结业成绩是自己收看到的信息,我们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完成了灯光考试后,还不算完,因为我们的学期是六个月,所以后面还有旗语、通勤、观察、电工课程。我们学完了灯光课,接着要上旗语课。所谓的旗语,就是一个人拿着两面红黄两种颜色的手旗,通过在人体上下左右不同位置比画表达出来的汉语拼音字母来发送文字的一种通信方式,也是靠眼睛看和脑子灵活辨别能力来完成。要想把二十六个拼音字母在身体各个部位上表达出来,并且还要迅速翻译出汉字,是一件更难做到的事情。
教旗语的教员是一个斯斯文文的人,姓马,个不高,不仅长得好看,而且脸上总是带着一副自信的笑容。他说:“学旗语,不仅能完成上传下达的任务,而且还能强身健体,是一举两得的课程,大家一定都能学会!”还没正式上课,他就给大家鼓足了劲。每堂课,马教员在我们前面比画,我们就在他前面大声喊着部位对应的拼音字母。他比画得越快,我们喊得越快。很快,我们都掌握了旗语的要领,那些拼音字母在身体各个部位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这下可把马教员高兴坏了,他说:“我教了这么多年的旗语,从来没有遇到你们这帮聪明的学员!”我们听了教员的话,就更加喜欢上了旗语,并且从拼音到后来一分钟收发二十个汉字,都成了不在话下的小事儿。就这样,我们的旗语课很快就结业了,成绩全都是优秀。
四
正当我们学习劲头十足的时候,我们小队接到了去农村“支农”的任务。大家都不清楚支农是啥意思?小队长说:“就是去附近村帮助麦收!”“麦收”这两个字,我不陌生,不就是割小麦吗?我们来自农村都在地里割过小麦,对此我们都不怕。可是,等我们到了地里,一没有镰刀,二没有其他收割工具,全靠用手拔小麦,这个太出乎我们意料了!用手把小麦一棵棵从地里拔出来,这是谁想出来的主意?没有人告诉我们答案,就这样,我们拔了两三天,汗流浃背,手全磨破了,最后终于帮着农民们把小麦从地里拔完,这才拖着腰酸腿痛的身体回到训练团。回到宿舍,战士们脱掉衣服就在太阳底下,用脸盆盛上凉水从头至脚冲洗,那个舒服劲儿,真是无法描述。
参加完支农,又开始进行队列训练。晚上,还要参加站岗任务。在那个年代,群众生活水平都低,附近村的农民总是翻墙进院偷猪食,我们不知道他们偷回去干什么,反正是经常上演猫抓老鼠的游戏。前面喂猪的战士刚把猪食倒上,后面就被村民偷走了,所以才导致训练团饲养的猪吃不饱食饿成皮包骨头。我们站岗执勤的任务之一,就是看守猪食的安全,不许村民偷猪食。训练团院大人多,我们好几次站岗都是轮在晚上。
一个人在离宿舍比较远的大院西南角上站岗,夜风呜呜响,夜鸟们哇哇叫,场景有些瘆人。因此,很多战友都不愿意站后半夜的岗,每次轮到我值日长的时候,我就有意把值班表上的时间做个调整,我主动去站后半夜,并且总是比其他人多站十分钟。其实,站后半夜岗,我也很害怕,尤其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一个人在猪圈区域巡逻,有时候会静得出奇,有时候会突然冒出一只猫头鹰叫声,令人惊悚胆怯。为了给自己壮壮胆,我就想到了唱军歌,我一遍又一遍地唱,一来是想通过唱军歌告诉那些越墙入院的人:我在此,不可轻举妄动;二来是唱军歌可以打发时间,还能给自己鼓足信心和勇气。还别说,从我站夜岗唱军歌那天起,再也没有发生偷猪食的事了。现在想起这事,我都佩服当年的自己!
由于我的工作表现好,训练团三大队给了我一个大队嘉奖。理由是:“该同志表现突出,思想进步,主动做好人好事,在尊干爱兵周中被评为尊干爱兵模范。”
中队长宣布嘉奖我时,我特别意外,我的陆军战友和海军战友们更是惊羡不已。
我们信号专业最后一门是电工知识课,教我们电工知识的是一名早我们几年老兵,因为他的电工知识好,所以留队当上了教员,我们从他那里又把学校里学到的电工知识温习了一遍,也很快完成考试。
就在大家都忙着结业下连队的时候,战友徐玉洲找到了我,他说:“我老家是掖县平里店公社洼徐村,我妈姓徐是本村人,我爸姓李是外村人.当初我妈为了在村里干大队会计,就让我从小跟她姓。现在,我想趁着下连队前把姓和名都改了,请你帮我想想改啥名好?”我听了既兴奋又好奇,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但好奇之后还是想帮战友出谋划策,我说:“让我想想,改就改一个比原先更好听的名字!”徐玉洲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我,说:“我等你想出来了,我就去改!”我答应着他,经过一番查字典和反复推敲之后,我找出了一个“韡”字--指光明美丽的样子,加上他的姓,就叫李韡。我把我的研究的成果告诉了徐玉洲,他一听立即高兴地跳起来,说:“我这就去找领导,改名字!以后,我就是李韡了!”
海军战士跟我们陆军战士不一样,我们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他们是结业后再进行分配,有的去海岛,有的去城市,具体分配去哪儿,得看结业成绩来定。当然了,也不排除个别人平日给领导种下好印象的,即使结业成绩不算太好,也能分到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
五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是我们完成学业离开训练团的日子。这天天清气爽,十八中队的李队长、王指导员、施小队长以及各位教员都来给我们送行,当时的场面真有一番难舍难分的感觉。教通文课的于教员握着我的手直说:“如果你是海军的话,就把你留下来当教员,接我的班了!”我说:“于教员,我们单位也有训练队,我回去也可能像您一样当教员的。”于教员说:“那就好!那就好!真希望如此,保持联系!”
就这样,我们结束了六个多月的信号专业学习,要返回自己的部队了。我回部队后,被调到码头炊事班帮忙,我眼看着所学专业没了用武之地,心里十分纠结惆怅。有一天,我接到门卫的电话,他说:“一个姓冯的海军军官来找你。”我一听吃了一惊,是谁?我就认识冯教员,怎么可能是他?我赶紧跑到门卫室,一看果真是冯教员,他身穿海军军官服英俊挺拔,他微笑着走过来跟我握手。他说:“今来青岛办事,路过你们这里,一是想来看看你,二是想把随身带的包儿暂放在你这里,等我办完事再来取走。”他见我在炊事班里干,很是不解,他说:“你的专业这么好,干炊事员不是太可惜了吗!”我无法正面回答他的话,只是告诉他这可能是暂时的,以后也许会有调整。我找到中队文书帮助冯教员把包锁在储藏柜里,然后送冯教员离开了营区。
现在想起来我都后悔,那时候怎么没有请冯教员吃口饭呢?他那么多海军战士学员,怎么没有去找他们反而偏偏来找我呢?
后来,冯教员办完事来取包的时候,中队文书赶巧不在营区,我一时找不到钥匙急得够呛,我用了一把别的钥匙捅了几下储藏柜的锁,结果居然把锁打开了,冯教员为此特别感谢我的急中生智。这次送走冯教员之后,我们再就没有联系过。找我帮忙改名的李韡,先后来找过我两次,我们坐在船甲板上聊天,聊训练团的往事,也聊个人的事儿。我也去他所在的青岛市莱阳路8号看过他,我们从信号台上聊到他的宿舍,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后来他托了关系改了专业,我们再就没有联系过。
现在再回想起北海舰队第一训练团学信号专业那段往事,就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浮现,李春生队长、王士亮指导员、施大安小队长、于教员、史教员、马教员,他们如果都还健在的话,应该都有八九十岁了,冯强教员也有七十多了,当年找我改名的李韡和那些参加信号专业学习的陆军和海军战友们,也都接近六十岁了,大家都过得好吗?
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就想把难忘的训练团记录下来,留住那段属于我们的青葱岁月。
原创文章,作者:芒小种,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fhgg.net/shenghuobaike/46175.html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食趣网】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fhgg.net/